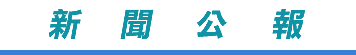
************************************************
以下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今日(星期四)在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发表的声明全文:
主席女士:
感谢各位今天给我这个机会解释我不检控胡仙女士的决定。
1998年3月23日,我向委员会汇报待《英文虎报》(下称《虎报》)三名被告人的案件审结后,我希望情况能容许我发表公开声明,讲述我决定不检控胡仙女士一事。该案在1999年1月20日裁决,现在我认为应该解释此事。在我谈论事件的实质内容之前,我需要先说清楚一些基本问题。
有人指摘我在案件完结后,没有意图去解释,又有人说我一直在拖延。首先,我要反驳这些指摘。我一直最关注的是我不应该令被判罪的人的上诉受到影响,或令到廉政公署进一步调查可能导致的任何审讯受到影响。
1999年1月20日(星期三)法官宣读判词后,律政司向报界发表声明,表示本司会小心研究裁决理由,并会考虑负责检控的律师对这宗案件的报告;如有需要,更会研究审讯过程的誊本。声明又称律政司希望不久就可以作出公开声明。至于何时发表声明,则要视乎有人可能对定罪判决提出上诉,而因此需要考虑的事宜。
在声明发表之时,尚未清楚宣判后被告人如果提出上诉,是否会引出一些需要考虑的事宜,令致我不适宜对此案有所评论。研究过多份文件后,得知情况并非如此。我在1999年1月23日已把情况告知委员会秘书。
同时,我也告知委员会秘书我正等候廉政公署的报告,以确定是否有进一步证据我需要考虑。廉政公署得到我的同意,要求会见三名被定罪的被告人,并希望他们的代表律师在上星期末或本星期初确实回覆。因此我当时同意今天到这里来。虽然目前仍未收到他们的律师的答覆,但是公众对此案的关注令我决定今天需要向各位作出声明。
我也希望重申去年我向委员会指出,我当时不解释我的决定的两个理由。首先,基于一贯确立的政策,律政司不会详细披露决定不检控某人的理由。稍后我再解释这项政策的根据。第二个理由,是在审讯完结之前,我不可作出任何评论,以免公正的审讯可能受到影响。在审理中的事项须受到这些限制,也早已确立。
由此可见,我决定直至今天才作出声明,并非企图拖延时间,只是严格遵守一些一贯确立的原则。因为有这些原则,香港的法治才有保障。
审讯
审讯中,赖磐德法官裁定《虎报》一位前雇员(黄伟成)和两位现职雇员(苏淑华和邓昌成)串谋诈骗的罪名成立。苏淑华和邓昌成同时被裁定六项伪造帐目罪名成立,黄伟成被裁定四项伪造帐目罪名成立。三人被判监,但是他们可能上诉,请各位议员留意这点。
串谋诈骗的控罪指三名被告人,在1993年至1997年期间,在香港与胡仙及罗浩然串谋 ─
向《虎报》购买或可能购买《虎报》及《星期日虎报》广告位的公司、商号或人士诈骗,即不诚实地─
(1) 促使《虎报》印刷超出真实、所知或预期所需数量的《英文虎报》及《星期日虎报》,藉以夸大该等报纸的发行量;
(2) 透过晨星有限公司购买多印的报纸;
(3) 改晨星有限公司及《虎报》的文件、帐目及记录,藉以为晨星有限公司提供营运收入,使该公司看来是购买了多印的报纸;
(4) 明知没有真实的基本交易而改《虎报》的文件、帐目及记录,以显示晨星有限公司看来购买了多印的报纸;
(5) 向英国出版销售公证会出示虚假的出版商平均净发行量申报表,其中包括看来是卖给晨星有限公司的报纸数量;以及
(6) 把看来是由晨星有限公司购买的多印报纸当作废纸处置。
上述六项控罪详情构成支持证明串谋诈骗罪的六项外在作为。
在控罪中列为同案串谋人的罗浩然先生,获特赦后,在检控三名被告人的审讯中作证。胡仙女士并无受审,只是作为未有被公诉的同案串谋人。1998年3月23日我出席委员会会议时,已经谈过这种情况如何发生的几个例子。赖磐德法官在他的裁决理由中,这样解释 ─
“在我转谈别个题目之前,适宜说明我一直考虑的问题:被告人是否与胡仙串谋,而非胡仙与他们串谋。我想对于不大熟悉刑事法的人来说,这个分别可能会引起初步的疑惑,而我预期他们会问,法庭怎能够说甲与乙串谋,而乙不与甲串谋,答案是根据证据法,某些证据只可指证某些人士,而非其他人士。
让我来举个例子:如果甲在法庭以外供认他犯了罪,从常理看来他会被送上法庭,凭借他的供认指控他。如果甲说乙也犯了同一罪行,那么,除非甲转为控方证人,否则不足以把乙起诉提审。在法庭以外某人关于你的评论,而你当时不在场质疑、验证或反驳他,不能用作证据指控你。显然理应如此。这项规定所根据的常理和公平原则,早已成为我们的法律的一部分。
换了胡仙,情况也是一样,胡仙的刑事责任从来没有、也从来不应该成为今次审讯的一个争议点,因为今次审讯纯粹集中在三名被告人是否有罪。审讯一直是围绕三人做过什么而不是胡仙做过什么。因此,审讯中所提的,只限于那些与这三名被告人有关的证据。
这个问题的最后一点,是检控人员在草拟串谋控罪时,有一种确立了的做法,就是如果有某些证据指控某名被告人确有串谋其他人,则这些人的姓名会在控罪中列明(见Archbold 1998第33-42段)。这种做法是基于对被告人公平的考虑,使他知晓他要面对的指控的详情。被告人的利益,要优先于被公开点名但非属诉讼程序一方的人士的利益,即使这使人士,因为不属诉讼程序的一方,而无法在审讯中为自己辩白。”
检控政策
香港、英国,以至其他普通法司法区,向来都奉行不详细披露检控决定的原因的政策,这项检控政策行之久远。不过,究竟有没有充分证据检控,而提出检控又是否符合公众利益,这些适用准则却可披露。不披露检控原因的政策的理据,英国的刑事检控专员,御用大律师Barbara Mills于1992年5月29日在致大律师公会主席,御用大律师Anthony Scrivener的信件中作了阐述 ─
“公众有权知道官方检控当局处理案件的原则,我们作出决定的理据,也应该向公众概略地指出......但再进一步提供个别案件的详情,则并不正当。决定检控和决定不检控,我觉得在此并无分别。相信你一定会同意,我不宜讨论决定检控;因为这样做违反保密原则,有损涉案各方 ─ 证人、受害者、被控人或受疑人的利益和声誉。如果聆讯尚未展开,公众的讨论可能会影响审讯。......同样,我也不能公开讨论不检控的决定,因为这样会等同审讯受疑人,而又剥夺他受法庭审讯时所会得到的刑事法律程序的保障。因此,从事公开讨论有关人士何以最初会受到怀疑,是荒谬和不公平的。”
1992年2月,当时的英国检察总长御用大律师Patrick Mayhew以同样的理由回答下议院─
“如果某人尚未被检控或控方已停止检控某人,则若继续进行检控所会引用的证据,便不该公开展示,这点极为重要。”
我和这些法律界前辈抱相同的信念。有关政策一向在香港实施,这是一项公正不阿,对受疑人公平的好政策。正如我在1998年3月23日向委员会解释,这项政策不是为方便律政司司长而制订的。这项政策之所以存在,是要保障刑事司法体系的健全、保障涉案人的合理权益,以及确保被告人在刑事审讯中,所会得到的基本保障不会在非司法研讯中被剥夺。因为在这种研讯中,并没有证据规则,没有无罪推定,没有盘问的权利,也没有“证明至无合理疑点”的规定。我绝不会认同那些赞成由舆论审讯的意见,又或者那些要求把证据交由公众辩论,从而决定某人有罪与否的意见。在我们珍视的司法制度下,向来只有法院才是判定受疑人有罪抑或无罪的神圣之地,而受疑人也有权根据刑事审判规则得到公平审判。此刻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我即将偏离一项多年来维护香港司法公正的政策。我必须强调:我这次偏离这项政策并非要造成先例。日后除非证明情况确实特殊,否则不会再对其他案件披露详细原因。律政司会局限于概括的回应。不论受疑人被检控与否,他们仍然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我必会坚定不移地维护他们的权利。
不检控胡仙女士的原因
现在,我准备披露不检控胡仙女士的原因。我这样做的原因有三 ─
(1) 外界对我个人诚信的指摘,我不能置若妄闻,必须加以解释;
(2) 要公平对待胡仙女士。胡仙女士于1997年6月4日与廉政公署会面的记录,很遗憾被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外泄给传媒。被声称可以指控她串谋的证据,已经广为人知,更成为公众的论题;
(3) 外界指我基于不当的考虑因素而作出决定,这种指摘可能已经造成不良影响;更有说法认为这已动摇了香港以至国际间对我们法律制度的信心。我责无旁贷,必须澄清,上述忧虑是没有根据的。
这宗审讯控方案情的概况
这宗审讯的控方案情指出:自1994年开始,《虎报》和《星期日虎报》的发行量三年多以来经常被大幅夸大。控方指称,《虎报》总经理苏淑华、发行总监黄伟成及财务经理邓昌成是夸大销售量计划的主脑人物。
报章的收入大部分来自广告,而报章的发行量是广告商的参考指标。出版销售公证会是一间英国公司,该公司会为使用其服务、遵守其规定和符合核数证明的报章证明发行量。《虎报》是出版销售公证会的客户。控方指称,出版销售公证会从《虎报》所得的数字遭虚报夸大,有关人士并伪造文件以免被识破。
报章的印刷量必须与夸大的数量吻合,不编印足够数量的报纸很难夸大发行量。虚报会出现两大问题:报章既确实未售出,如何能令帐面显示多印的报章已经正当卖出,与送交出版销售公证会的数字吻合?而未出售的报章又如何处置?
为解决第一个问题,有人购入晨星公司,由《虎报》雇员营运,藉晨星公司订购报章的名义向该公司发出帐单;然后由晨星公司的户口开出支票付帐;用以支付这类报称交易的金钱,实际来自《虎报》,有关人士通过伪称《虎报》曾选用晨星公司提供的虚构服务,藉此向晨星公司缴付服务费。这项安排称为“对销发票”。晨星公司向《虎报》发出伪造订单,误导核数人员。
晨星公司并不是唯一一间用假帐来掩饰有关勾当的公司,另外三间与《虎报》关系友好的发行商也曾各自与《虎报》达成类似的安排。他们虽没有购入或收取《虎报》,却会收到帐单,但他们清付帐单的支票尚未兑现之前,《虎报》便会开出数额相同的支票,用以支付这些发行商从未提供的虚构服务。
至于多余的报章,有关人士则利用晨星公司租用货仓存放报纸,由承办商搬运报纸存仓,一星期或个多星期后再把报纸运送至湾仔码头作废纸处理。
当廉政公署发现有大量近期的《虎报》以上述方式处置时,即介入调查。在1996年8月14日托运的货物中,发现内有14 000份《虎报》。该署认为这是一宗不诚实的事件,也就是有人藉发行量行骗。廉政公署采取行动之后,晨星公司报称的销售数字也立即下跌,但整体发行量没有相应下降。《虎报》继续遭人当废纸处理,而调查则显示报章售予三间关系友好的发行商。
苏淑华、黄伟成和邓昌成因此被控串谋诈骗,此罪只与晨星公司夸大《虎报》发行量有关。他们也因为向出版销售公证会提交的申报表,而被控以伪造帐目的实质罪行。这些实质罪行仅与三间友好发行商夸大数量一事有关。
以上大致为这宗案件的控方案情。
有关三名被告人的控方案情
律政司向三名被告人提出检控,各有不同依据。法官扼述案情如下 ─
(1) 苏淑华:她接受廉政公署问话时承认在这项计划中的角色;苏淑华的下属孙敏珍,提供有关晨星公司的作用、可导致苏淑华入罪的资料,公司的发行总监罗浩然,获特赦后作证,表示他曾与苏淑华交谈过,她指示他夸大有关数字;公司前任总经理Jim Marett指证苏淑华,说曾经谈及夸大数字的事宜;有关情况和当时的文件,也显示她自知有份参与。
(2) 黄伟成:他接受廉政公署问话时承认他在这项计划中的角色;黄伟成的下属罗浩然及另一名雇员王提出的证据,确证了他的行为,即有关控罪的核心内容;正如法官所说,罗浩然及王
“的证据,明确显示他对虚报销售量以掩饰扔弃了的报纸数目起一定作用。”[法官补充说,“两名证人提供的有力证据让我无需考虑全部有关(黄伟成)的其他证据,而这些证据肯定存在。”]
(3) 邓昌成:他接受廉政公署问话时承认曾参与其事;他身为前任发行总监,夸大发行量及扔弃报纸证实确有其事;他所负责的文件;以及他与晨星公司的密切关系也构成了证据。
我无意再多谈论三名被告人,因为他们可能会上诉。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也不必这样做。我已经清楚说明每名被告人的控罪范围。我不难就此总结说,我们有充分证据,把苏淑华、黄伟成和邓昌成提交审讯。
不提出检控的理由:一般考虑因素
我跟谈到胡仙女士,她当时和目前都是上公司星岛集团主席。星岛集团拥有多家附属公司,大部分涉及出版业务,《虎报》是附属的出版公司。
我于1998年2月23日决定不该检控胡仙女士时,我考虑过有关她的证据,其中包括廉政公署1997年6月4日的会面记录。从一开始,我便觉得廉政公署所提交有关胡仙女士的证据,显然远不及另外三名受疑人的实质。也从没有证据显示并非这样。值得注意的,是罗浩然没有指证她牵涉在内,没有其他证人指证她牵涉在内,没有商业记录或文件指证她牵涉在内。基于这种情况,我问自己是否有充分证据提出检控?提出检控又是否符合公众利益?为此,我听取顾问的意见和审阅胡仙女士代表律师的申述,再加以适当衡量。我是经过非常仔细评核有关证据、意见及申述后才作出决定的。
在谈论具体的考虑因素前,我想强调一点,检控人员决定提出检控,通常远较决定不提出检控容易。不过,最重要的,是检控人员必须敢于按自己的信念行事。在涉及公民自由这尤关重要的事情时,检控人员更是责无旁贷,必须细心评核有关案情。他们不得轻率处事,推搪说“交由法庭决定吧”。这样做会构成敷衍塞责。除非有明显的证据,支持应该提出起诉,没有人应该受到刑事审讯 ─ 审讯难免会为受审者带来难忘的痛苦。这是最基本的原则,我从不容许偏离这原则。我完全明白前任英格兰及威尔士律政专员Lord Howe of Aberavon御用大律师刊于1998年10月26日《泰晤士报》的文章所指,他写道 ─
“我体会到,赋予律政专员维护法治的酌情权与责任,不但容许,有时更要求我不得进行某些检控。”
在考虑有关会面记录时,我紧记刑事诉讼程序必须遵行的严谨验证准则。控方有责任证明案情无合理疑点。再者,《刑事检控政策》小册子(1998年)第13段清楚订明 ─
“律政司司长并不支持单凭表面证据即足以作出检控决定的见解。”
我需要决定的,是是否有达至定罪的合理机会。这是一项必须细心衡量的判断,然而由于没有其他证据,经整体衡量她的会面记录后,我并不认为有这个达至定罪的合理机会。
不提出检控的理由:证据
我不打算逐一讲述胡仙女士接受廉政公署问话时作出的每一项答覆。总言之,会面记录必须整体审阅 ─ 当中共有224条问题和答覆 ─ 而不该单独引述一、两项。我紧记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虽然开脱罪责的资料的作用不及罪性资料,但仍必须把会面记录整份审阅。孤立地看几条问题和答覆,是不正确的做法。我看过整份记录后认为,虽然胡仙女士希望提高那两份报纸的发行量以吸引广告商,但她一再强调,她无意欺骗英国出版销售公证会,而这是三名被告人的控罪中所指的外在作为之一。虽然同意多印报纸可以提高发行量,但她对有关详情不知晓,而全部交给苏淑华处理。她对购入晨星公司一事全然不知,这是三名被告人的控罪中所指的另一项外在作为。胡仙女士称对改文件或伪造帐目事件亳不知情。我确实觉得,三名被告人所作的一切,全然超出了胡仙女士的原意。胡仙女士从廉政公署得知这些事情时,清楚表示她对构成伪造帐目的行为一事全不知情;更坚称假如她知道这事,一定不会容许这样做。根据该份记录记载,当胡仙女士于1996年8月从廉政公署得知有关行为并不合法后,她告诉其他人停止多印报纸。她得知多印的数量时,看来真的吃了一惊。胡仙女士或者早该加强对下属的督导和管理。她或者也不够审慎,就让下属推行一项含糊不清而她理解为“临时”的促销计划,而没有去详细了解其中涉及的具体考虑,也没有正确评估她所同意的目标可能产生的影响。然而,她说并不知道下属自行作出了违法的作为(而法官亦判定是由下属自行作出的),而得知后已经命他们不要这样做。这点没有互相矛盾的地方。我一再寻找证据,看胡仙女士是否涉及三名被告人被控的串谋罪中的各项外在作为,但我找不到这样的证据。我在此必须一提,胡仙女士身为集团主席兼公司董事,不单只监督《虎报》的业务,《虎报》只是公司的附属公司之一,她还要监督公司的其他营运情况,遍及印刷、物业发展和置业、控股投资、财务及一般管理。我相信有一点起码可以提出争辩的,是她实在业务太繁重,肩负太多工作而没有适当监察下属的行为。她甚至不能够记起是否曾经听过晨星公司的名称。经再客观研究这宗案件,最后也不能令我信服,胡仙女士的行为确实构成诈骗行为;换言之,我不信纳她在知道自己没有权利这样做的情况下,曾经作出不诚实的行为损害他人的权利,或冒险损害他人权利。如果我授权控以胡仙女士串谋诈骗罪行,便是有违刑事检控政策。
至于苏淑华、黄伟成和邓昌成罪成的各项伪造帐目实质罪行,全然没有证据指证胡仙女士牵涉在内,也从没有证据显示并非这样。
有人提议,若有一些针对胡仙女士的证据,我便应该检控她。审讯期间可能会出现多些证据;被告人会有机会解释本身的行为;法庭届时可以裁定她是否有罪。我必须反对这样做。正如我之前所强调,除非有明显的证据,证明应该提出起诉,没有人应该受到刑事审讯。反过来说,即使法院最后裁定被告人罪名不成立,但被告人已经经受痛苦,支出法律费用,声誉和信誉也会受损。因此,若只为了律政司司长免被怀疑,而在没有充分证据达至“合理定罪机会”的情况下提出检控,只会造成司法不公。
有些人认为,既然胡仙女士从有关罪行中得益,她就要对此负责。然而,串谋罪的定义是两人或多人协议进行一项非法行为,并意图付诸实施。各人必须明知所协议的行为确实非法,而有意图把这个非法的元素实施。由于有关胡仙女士的证据 ─ 即使以最强的评估,也未能符合上述准则,我不会基于猜测而提出检控。我刚才总结说,如果没有达至定罪的合理机会,我提出检控原则上是错误的。我也不会纯粹为逃避公众批评而作出决定。
不提出检控的理由:公众利益因素
我曾收到胡仙女士代表律师的书面陈述,并认真考虑其内容。结果我认为从公众利益眼,不应该检控胡仙女士。星岛集团当时面对财政困难,正跟银行商讨重组债务,如果胡仙女士被检控,显然对重整计划造成极大阻碍。如果集团跨台,其属下的报章(包括香港仅有的两家英文报章之一)很可能被迫停刊。我想在此作一些补充:在1996年年底、1997年和1998年,本港已有好几份报章刊物先后停刊。一间颇具规模和重要的传媒集团在当时倒闭,除了引致雇员失业外,很可能会给海外传达一个极坏信息。正当本港失业人数不断上升,若在这时候作出检控,可能会引致更广泛的裁员,这点令我感到不安。在这情况下,我的首要责任,是考虑检控其他人可能出现的后果;其次,是我必需问自己:提出检控所可能带来的后果,与所指称罪行的严重性比较,两者是否相称。我认定两者并不相称。一个重要传媒集团在当时倒闭,除了打击本地士气外,还可能给国际社会传达错误的信息。因此,我认定对胡仙女士提出检控,并不符合公众利益。我再问自己:该否基于公众利益,撤消对其他三名受疑人的检控批准?我决定不应该撤消检控。
覆检不作出检控的决定
各议员或许会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就是自此之后,我是否不再考虑会否检控胡仙女士。答案是“不”。我清楚了解,支持我作出决定的每项理据,情况均可能改变。事实上,鉴于胡仙女士和该公司本身情况的改变,在今天来看,我在1998年2月23日曾纳入考虑的公众利益因素,重要性已经减少。至于证据方面,若发现进一步的证据,我会乐于考虑这些新证据,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因此,我在1998年3月19日曾请刑事检控专员通知廉政专员,若审讯中发现任何足以指证胡仙女士的新证供,我乐于覆检原先不检控胡仙女士的决定。刑事检控专员把我的意见转告廉政专员。此后,我一直准备考虑来自任何方面的新证据。
该案在1999年1月20日审结后的几天,我和顾问曾研究法官的裁决理由、负责检控工作的外聘大律师的案件报告,以及审讯誊本的摘要。然而,审讯中并无出现新证据,足以支持我须覆检最初不检控胡仙女士的决定,虽然案件有53名证人亲自作供,还有接近3 000页证物记录。1999年1月22日我也得知,据廉政公署所知,审讯中没有出现新证据足以指证胡仙女士串谋行骗。正如主审法官指出,“审讯一直是围绕他们(三名被告)做过甚么,而不是胡仙做过甚么。因此,审讯中所提的证据,只限于那些与这三名被告人有关的证据。”
案件于1999年1月20日审结后,廉政公署寻求批准,进一步调查此案。我已批准廉政公署的要求。有关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我正等候廉政公署提交最后报告。因此,各议员定会明白,我不能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阐述。
结论:基于真诚作出决定
以上就是这件案件的背景。即使从事后来看,若要重新开始,我也不会采取别的做法。我已经明确地向公众交代不检控胡仙女士的详细原因。关于在这案件所采取的立场,我所披露的资料,远较殖民地时期任何一位律政司,甚至英国任何一位律政专员为多。我提出的理由,或许会受到批评。另一方面,我也会因透露太多资料而被指摘。我必须说明,决定某人是否有罪,是法庭的责任,要我公开谈论某人是否有罪的问题,我感到极不愉快。我仍然深信,受疑人的权利,应该获得最充分的保障。不过,议员要求我在委员会交代我的行动,而因上述特殊情况,我已经就事件作出交代。我请委员会接纳我的保证:无论何时,我都是基于真诚行事。我并无受到任何压力而作出有关决定。我所作的决定并非基于任何人事关系或政治身分。一直以来,我均严格遵守律政司确立的检控政策和《基本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我已经向委员会交代我的立场。我希望议员会感受到,我的解释是坦白和诚实的。我希望委员会接纳我的解释,并拒绝接受与上述解释不符的猜测或报告。
最后,我请议员留意《基本法》第六十三条的涵义。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这就是说,检控的决定,不得基于任何方面的外来压力。律政司司长绝对不能轻率处事,纯粹因满足公众或受外来压力而检控某人。也即是说,律政司司长须就检控的决定负起个人责任。今天我就有关的不检控决定作出解释,这项决定曾令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受到相当的批评,我感到十分遗憾。我愿意就所作的决定负起个人责任,基于这点,我今天出席委员会作出解释。
完
一九九九年二月四日(星期四)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