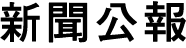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医学讲座教授及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及控制合作中心创立总监抗疫记者会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举行记者会。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医学讲座教授及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及控制合作中心创立总监梁卓伟教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卫生署署长陈汉仪医生、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和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亦有出席。 以下是梁卓伟教授的开场发言:
感谢行政长官,各位传媒朋友你们好,先和你们拜年,希望我们香港人可以身体健康,亦在面对今次这个很严重的疫情,我们在香港可以保护香港市民的健康。
首先我想向大家交代在科学方面或医学方面的一些基本资料。大家都知道其实在过去这星期,我们不同方面的团队在不同高等教育的研究机构亦在进行大量工作,包括在临床方面、包括在公共卫生方面、包括在流行病学、包括在微生物学,亦包括一些无形的估算,这些团队综合了多个研究得到以下一些初步结论。
我将分三方面和大家说说──第一方面是传播力transmissibility;第二方面是临床严重性clinical spectrum of severity;第三方面是在检测方法和临床的一些基本资料。
首先说说传播力 。传播力其实在过去几天,大家可能知道世界卫生组织亦为这个在武汉开始的疫症开了一个紧急委员会会议称为emergency committee,是世卫总干事去决定究竟会否宣布或颁布这疫情已经达到所谓的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或者称为PHEIC的定义,当中亦有一些供大家参考有关传播力的资料。我们自己的团队亦在进行或做了一些研究,大家都知道我们上星期亦发表了其中一个数学模型。综合多方面的研究,亦在我手上的最新资料──昨晚我们亦和世卫总部及全世界十多个不同国家做流行病学模型的团队交流意见──综合来看,我们的基本繁殖率或大家叫”R nought”,在这个疫情大概我想如果看中位数是差不多是2,即是每一名染病病人会平均传播给两名其紧密接触者;即是说每一个病人会衍生出两名染到这疫症的其余病人;而引生到疫情的doubling time,亦即是它需要多久令感染数字倍增,大概现在来看约一星期左右。
这是一个甚么启示呢?简单来看,如看十七年前「沙士」疫情,这次和它是差不多。「沙士」在最初期基本繁殖数亦是2至3,而它的doubling time,需要多长时间去把感染数字倍增,都是七至八天,所以这绝不比当时「沙士」疫情弱。
第二 ,在十一年前,在我们零九年猪流感大流行的时候,它的基本繁殖率其实是1.4至1.5左右,所以相比起我们今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反而更低,但是因为它繁殖的代数,亦即是它的generation time,是冠状病毒的一半或六成,所以变成它的感染数字、它需要倍增的时间,只有四天。所以,它的基本繁殖数没有那么高,但我们现在看到它倍增的时间是差不多双倍。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比较之下,总括来说这疫情是绝对绝对不能轻视、是严峻的。
说完这些,我们需要看这个基本繁殖率和它的doubling time,只不过是说假如没有任何干预措施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它会用这样方法繁殖,但是现在香港其实未有任何(资料)显示我们本土有自己的传播。我们已有输入个案,但是在输入个案当中未看到有证据显示它会令我们本土有持续的传播,所以我们现在的策略应该是继续去维持这个「围堵」的策略containment。
Containment的意思是希望在第一时间,假如有任何输入个案,会第一时间把它隔离治疗,令它不会平均每一个患者之间便可以传给两名患者,在它还没有传给两名患者之前,假如你已经把它隔离和治疗,这是我们现在应该继续围堵的策略,但是我们亦要承认、亦要明白病毒无疆界,亦不可能靠任何一个政府或任何地方可以命令它停。正如猪流感的时候,大家亦记得,我们的围堵策略是由当年五月一日劳动节开始,我们第一个输入的病人是从墨西哥来的,我们用围堵的策略成功将它拖延到四十天后才有第一宗本地传播个案,所以我们同样地看,希望这个疫情可以完全成功围堵,并一直维持至疫情慢慢减退,但如果万一没有办法可以完全围堵,可能亦会迟早有一个本地的传播,这我们亦需要有心理准备。
第二方面是临床的严重性。早前在36小时前,我们亦在Eurosurveillance,即是一本学习研究期刊,已经发放了我们一个数据,就是说假使你患病而需要住院,你的死亡率大概是百分之十四,即是每七至八位需要住院而染到这个病的病人会因这个病而死亡。对比在「沙士」期间,或者任何其他非典型肺炎个案需要住院的都是类似──「沙士」期间,香港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十七。但这绝对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case fatality ratio,我刚才说的是hospitalised fatality ratio或是hospitalisation fatality ratio,是建基于所有病情严重至需要入院;但如果你说「沙士」与今次不同的是,「沙士」时假如你染上了这种「沙士」病毒,你是差不多百分之一百都会发病,而发病的严重性是需要入院治疗。所以在所谓的隐形病人在社区内,差不多他并不会持续地隐形,即是他迟早染病他都会发病而需要入院治疗。在这个我们初步临床资料显示,在过去刚刚24小时,在刺针医学期刊,亦有包括我们香港团队袁国勇教授所带领的团队,亦看到似乎那个clinical spectrum包含了多些隐形个案或是轻微病征个案,而如果这些轻微病征个案其实一不留意,他可能根本没有需要入院治疗,而他自己可能亦会痊愈。所以变相他可能传播亦有潜在风险,但与此同时,因为多了一些轻微个案,变成除以死亡率,整体死亡率其实一定不会有百分之十几那么高。
第三方面要说的是检测方法或者临床的基本。如果大家回看由曹斌教授,他是北京一位非常出色的教授,在刺针亦发表了文章及袁教授发表的文章,其实大家都是异曲同工看到有不同的轻微个案,包括并不是每一个都有肺炎,甚至并不是每一个都是呼吸道感染。尤其是我们港大深圳医院那几个个案有部分是有发烧和腹泻,并不是一个呼吸道感染,所以我们大家要高度留意。所以这亦要回看,我们明白到检测的困难。
最后,就要再看看它的潜伏期,因为潜伏期亦很着重究竟我们隔离政策或是医学监察需要做多久?似乎现时综合各方面的证据,看到的潜伏期大概是六天,而上限,即是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患者是会达到十四,甚至十五或十六天,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潜伏期方面我们得到的最新数据。
向大家交代了科学和医学方面的数据,亦要说说为甚么我们今次在香港可以做得到所有以上我可以给到大家的科学和医学证据?其实都是有赖几个团队,他们自从「沙士」后开始十七年来不懈的努力,亦要说在食卫局的研究基金有一个名为Research Fund for the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RFCID)。它多年来都有做一些commission grant;卫生署亦特别为了新发传染病有一些commissioning,所以才会令到我们有现时的数据。卫生署亦支持我们自己去做一个世卫的协作中心,我亦因为这样才可以与内地和国际交流情报和合作。正如我所说,我们自己的团队,包括两间大学,都不停要向海外个案和内地有个案的地方与它们的专家交流,才可以得到这类情报和信息帮助香港抗疫。大家亦留意到,其实许树昌教授昨日亦刚刚主持卫生署的科学委员会会议,得出一些结论可以帮助我们去做这类事情。最后,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袁教授去了武汉,亦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我自己亦在过去的48小时带领了五个人作为一个团队前往北京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希望大家会明白及继续支持这一群默默耕耘的科学家和医生去做这些工夫。
再要说多一次,我们现时一定要用一个高度戒备,但要保持冷静的心情抗疫。我们现时还在一个围堵政策,在现时目前为止看不到有迹象说香港已经有本地传播个案,但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算我们现时做好所有措施不是万能的,是有可能会迟早有本地传播。假如有这样的一天,我们的策略将会变成一个缓冲或mitigation策略,不是可以把疫情停止,但可以把疫情减慢,令我们所有应变措施可以做得到。大家都会记得,其实在过去的猪流感亦是用这种策略。
作为一个公共卫生的医生,希望再呼吁几点。一,勤洗手hand hygiene;二,一定要有sneeze and cough etiquette,即是说当你喷嚏或咳时一定要掩着口鼻,为了你和你周围的人着想。第三,要打针,因为现时同时是流感高峰期,如果你打了流感针是好让我们的医护人员去识别,你应该已经受到流感疫苗的保障。第四,戴口罩,尤其是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譬如公共交通工具或是外出,这可以保障你自己和保障其他人。但我们要明白,戴口罩并不是万能,戴口罩也有正确和不正确的方法。很多人刚才都会看到,我亦看到在网上有很多不同评论,为甚么我们出来叫人戴口罩而我们并没有戴口罩?因为戴了口罩是没办法说话,一说话便要除下口罩,除下口罩也要先洗手,除下口罩折好后放进胶袋,接着再要用酒精洗手。我们要明白就算戴了口罩都要正确地戴口罩。最后,其实香港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近视是全世界最高,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轻微的保护,就是你那副眼镜。如果你幸运不用戴眼镜的话,可以考虑,尤其是在人多挤迫或在流感高峰期,可以去试试配一幅平光镜。这某程度上绝对不完美,但可以在某程度上保护到,(防止)一些飞沫传播。多谢行政长官。
完
2020年1月25日(星期六)
香港时间22时31分